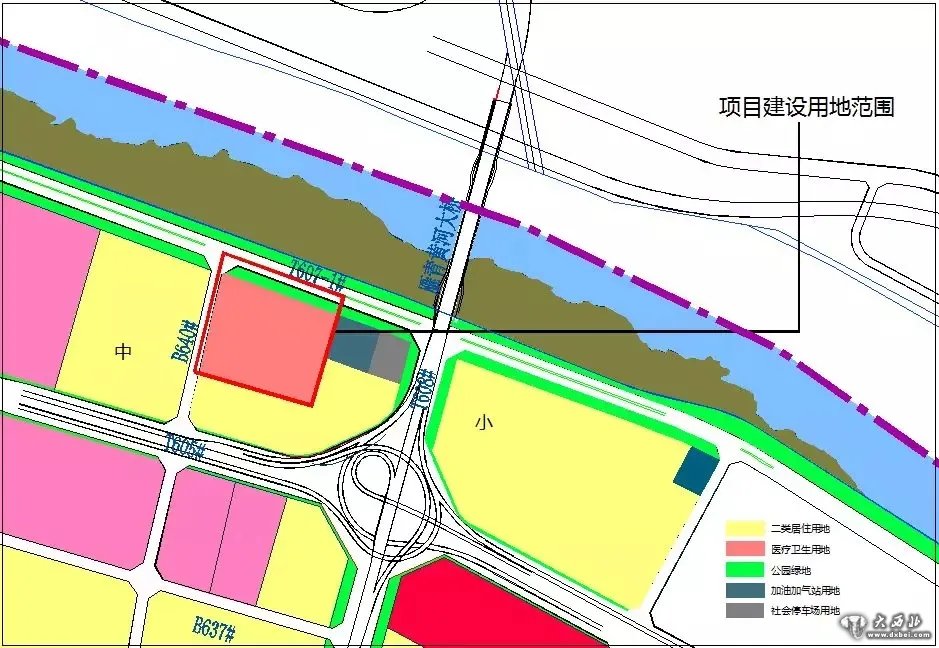2011年9月,深圳城管龚波在“执法”时被小贩刺死。事后,龚波一度被渲染为英雄,所在公司还为其申请“革命烈士”。日前,警方发现,龚波竟是某犯罪团伙骨干。他们披着城管外衣,对辖区商贩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目前,深圳全市参与城管外包的公司有35家。(8月6日《城市信报》)
执法权沦为敛财工具,龚波事件可谓是一次彻头彻尾的乌龙,负有直接责任的城管外包模式,也因此而面临停摆风波。据深圳城管局表态,近期内将会有新政出来,不排除彻底取消外包,这意味着这一一度被誉为先进的管理体制,将可能就此终结。
不管深圳城管体制最终何去何从,城管外包确实值得反思。城管外包取源于“西乡模式”,后推广至深圳全市,全国不少地区也有跟进。按照最初的模型,政府以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配备城市协管员,起初的协管员在职能上,是相对明确的,仅包括一些街道内的公共服务、园林绿化、市政设施维护,等等。用市场竞价赎买机制,来提升管理效率、专业度,进而为膨胀的政府职能瘦身,这符合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基本趋势。现在不少隶属于政府的职能,也都通过外包实现了社会化经营,大大减轻了成本,比如环卫工程外包。
但是,随着城管外包推开,安保或物业出身的协管开始全面参与终端管理后,权限问题也随之而来。严格地讲,城管职能并不具备市场化的全部要件,它本身就有点定位不清,既提供公共服务,也有权执法,介于服务与管理之间。而且在职能分工上,城管往往是大包大揽,任务冗杂,涵盖各个方面,于是,在外包过程中,为了便于操作,城管局往往将其终端职能统统打包,分派给了市场化的公司、企业,执法权因此在实质上实现了让渡,这是与《行政处罚法》明显相悖的。当不具备权力认证资质的协管人员,开始掌握赎买来的管理权限,城管外包已经埋下了深刻隐患。
更重要的是,“城管”本身就经过了一次外包,城管的职能、权限原本属于各个城市职能部门,后来这些职能、权限经过下放,并成立城管局予以吸收,城管才具有了执法权。那么,当城管将职能再度打包出售时,就有点像建筑领域的层层转包。二次外包的直接后果,是责任主体不明晰,城市管理部门将任务抛给城管局,城管局再抛给外包公司,原有的监管压力,被边际效应所稀释,处在链条末端、但却直接与社会接触的协管员,是最远离监督和管理的制衡的。一方面,他们不具备专业执法资格,短期培训即可上岗,有执法权力,却没有对等的责任意识,权责失衡,执法也就容易失范;另一方面,城管部门不是城市管理的直接参与者,出事后可将责任丢给一线协管,这削弱了其管理、规范执法队伍的动力,也是为何城管系统常出“临时工”的原因。
一般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市场化,首先是管理和服务的分离,外包的机构负管理责任,承包公司负责经营,二者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但城管相对特殊,城管部门作为外包者,同时又是承包者,于是,处在中间环节的城管部门,享受着其他部门下放的执法权及外包职能的便利时,却往往未能明确自身的管理责任,身份问题不可避免地造成管理混乱,权力也就有了异化的可能。深圳城管外包是否走向终结,目前尚无法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整个城管体制有必要彻底厘清,城管的身份、职能、角色,都需要有个更为清晰的定位。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