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同一时刻住在他家另一个房间的六姨妹也惊惶失措地跑了出来。凶手并没有理睬六姨妹,径直指向谭甫仁。谭甫仁跑到窄窄的小天井里,已经被挤在无处藏身的空间,王自正看准了谭甫仁进行射击。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用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方式死在一个亡命徒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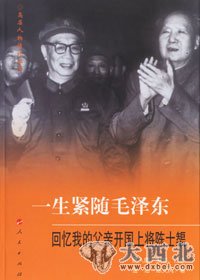
本文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口述:陈人康,整理:金汕 陈义风,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父亲与谭甫仁还要从井冈山说起
谭甫仁是建国以后被暗杀的级别最高的首长,他死在乱哄哄的文革中。他与父亲相识于1928年春季,正是父亲参加的新城战役。那一次仗打得干脆漂亮,一整营的敌人一个也没有跑掉,除了被击毙的以外,都成了教导队的俘虏。
我父亲当时在红四军教导队当区队长兼教官,战役结束以后所有的俘虏都交给了教导队看管。当时红四军有优待俘虏的政策,所有的俘虏都受到了良好的对待,有伤的会得到及时的治疗,他们身上的财物都由他们自己保管。红四军当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从这些俘虏中挑一些出身好且愿意跟红军走的人,把他们经过教育训练以后充实到红四军的连队中去。
一天,我父亲忽然听到楼上的俘虏中有人在唱《国际歌》。歌声引起了我父亲的注意,因为当时敌军兵营中是不能唱《国际歌》的,这首歌只有红军的部队里才有人唱。这个俘虏显然不是一般的俘虏,我父亲立即跑上楼去,想找到这个唱歌的俘虏。
《国际歌》有着神奇的魅力,父亲对我说过,他没有什么音乐细胞,但是他一生中有两首歌常常让他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一首是《义勇军进行曲》,因为在艰苦的抗战岁月和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刻,这首歌给了他那么多的鼓舞和联想。另一首就是《国际歌》,父亲说《国际歌》在鼓舞无产者砸碎旧世界而不惜牺牲一切方面真是登峰造极,所以列宁做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是知道《国际歌》在无产者中的分量的:“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父亲也正是听到了《国际歌》突然拉近了与这个俘虏的距离。
但看见我父亲上楼,歌声就停止了。我父亲只得发问:“刚才这首歌是谁唱的,请站起来!”
一个清瘦的青年俘虏起身答道:“是我唱的,长官,如果不允许俘虏唱,我就不唱了!”
我父亲说:“不,可以唱,你唱得很好。叫什么名字?”
那个青年说:“我叫谭甫仁!”
我父亲说:“你在哪里学的这首歌?”
我父亲这一问,谭甫仁立即变得眼泪汪汪起来。原来谭甫仁是广东梅县人,参加过澎湃领导的第二次东江起义。在那次起义中,他学会了唱《国际歌》。本来打算为了“英特纳雄耐尔”奋斗到底,没想到起义遭遇到巨大挫折,还没有取得什么战果就不得不随着起义部队四处逃散。
谭甫仁在逃亡过程中,到了江西一个地方。在饥寒交迫中,吃饭成了唯一的需求,无奈之下只得去军阀朱培德部当了一名士兵。这次谭甫仁随着部队来到新城布防,没想到竟成了红军的俘虏。
我父亲安慰了谭甫仁几句,并安排了他与东江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的朱云卿见面,因为谭甫仁参加过朱云卿的部队。朱云卿此时是红四军一团的参谋长。
谭甫仁高兴得不得了,立即给我父亲敬了一个军礼。
(2)谭甫仁指挥的炮声成为毛泽东笔下的千古绝唱
当即我父亲叫来传令兵,要他带着谭甫仁到团部去见朱云卿参谋长。朱参谋长跟谭甫仁可亲了,朱参谋长不但认识谭甫仁,还知道谭甫仁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东江起义中,朱参谋长和谭甫仁曾经并肩作战,多次出生入死。直到后来部队被打散,才各自不知去向。
我父亲吃饭时碰到了毛泽东,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一颗红色的苗子哩,现在该让他归队了,要把他要留在革命队伍里!”
由于父亲与谭甫仁的特殊关系,他多次向我讲述过谭甫仁的经历。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谭甫仁到工程兵担任政委。父亲在几十年的司令员生涯中,同几位政委合作的都不是太好,可能司令员和政委双方都有责任,这种格局在部队中是常见的。但是父亲说过,和谭甫仁合作是很融洽的,因为他知道政委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记得小时候我在家中常常见到谭甫仁坐在沙发上和父亲谈论工作,那时业余时间也都被工作大量地占据了。
父亲也向我讲过谭甫仁回到革命队伍后的事迹,他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士兵委员会干事,红十二军连政治委员,687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红十五军团第78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谭甫仁打仗曾经引发了一首被亿万人传诵、并将流芳百世的诗词,那就是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
那是1928年8月30日早上,国民党湘赣敌军4个团向井冈山扑来,妄图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举扼杀在摇篮中。当时部队弹药紧张,每人只有3至5发子弹,所以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这几发子弹,所以决定把敌人引入近距离再发射。由于敌人装备比我们好得多,如果攻上来会导致我们重大伤亡。团长朱云卿观察敌人已经很近,甚至他们士兵的表情都已经看见,他命令“打”,简陋装备的鸟铳、步枪一齐开火,由于距离近、敌人密集,真是做到了枪枪有人倒下,红军积攒了一些大石头也派上了用场,大家从高处掷下,大石头飞速滚动向下,敌人被砸得惨叫声四起,纷纷从羊肠小道两旁滚下山去,不是摔死就是伤痕累累。
敌人知道红军枪弹有限,在下午4点卷土重来,谭甫仁看看自己的枪膛,只剩下可怜的一发子弹了,只见谭甫仁大声喊道:“团长,前不久我们修的那门大炮呢?”
此时只剩下最后一发炮弹了,大家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几十斤重的家伙身上,谭甫仁憋住气命令:“放!”只听见炮弹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不偏不倚地落入密密麻麻的敌群,随着一声巨响,敌人血肉横飞,惨叫不断。敌人以为红四军主力回到井冈山,敌军害怕吃亏,赶忙逃回茶陵。
毛泽东得知,兴奋写下:“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而制造炮声的正是谭甫仁。
(3)谭甫仁中将被暗杀前几个月,我曾经拜访了简朴的谭叔叔
自从父亲与谭甫仁相遇,在以后的几十年间保持了很好的友谊。父亲说,谭甫仁是个难得的部队政治工作者,看他后来的履历,也大多担任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任115师教导第七旅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兵团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治委员,昆明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父亲对我说,他们那一代军人也许有这样和那样的缺点乃至不足,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非常敬业,个个都是工作狂。1959年谭甫仁到武汉军区后,就在想着政治委员如何做好加强部队的战斗力。尤其解放已经十年,在和平年代里部队还能不能居安思危,能不能有严明的纪律和顽强的作风。这就需要一个好的榜样,为了选好这个榜样,谭甫仁深入调查研究,他感到一军一师一团一营六连是一个很好的样板。他培育了六连继承和发扬了战争年代的不怕苦、不怕死的作风,1964年1月,国防部正式批准授予六连为“硬骨头六连”的荣誉称号。直到改革开放年代,这个闻名全军的先进典型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书写着自己辉煌的历史。
1977年1月,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向“硬六连”学习的号召,1984年1月22日,中央军委向该连赠送了“发扬硬骨头精神,开创连队建设新局面”的锦旗――而那时谭甫仁已经离开人世十多年了。
说到谭甫仁的去世,曾经给了父亲很大的震惊,因为这样级别的干部被枪杀在解放以后从来没有过。
在谭甫仁去世前一年,我正在云南健水二炮基地培训。尽管我的家庭背景部队首长也知道,但是在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照顾。部队的伙食是比较单调的,我特别希望能够有机会好好吃上一顿肉。
那是1970年春,18岁的我正是长身体、贪图吃的年代。当时部队派我到昆明,事情办完后,我很想到谭叔叔家改善一下生活,于是直奔昆明军区。警卫看到一个小孩子找政委,有点怀疑我是故弄玄虚。我很自信地说:“你就告诉谭政委,我是陈士榘的儿子,我父亲让我来看望他。”
谭甫仁接到电话很快让我进去。他见到我很高兴,摸了摸我的军帽,拍了拍我的肩膀,他说:“我和你爸爸也是这么年轻就穿上了军装。”他又问我是家中的老几,我告诉他老四,他感叹地说:“小孩子长得真快,我们怎么能不老呢。”
他询问了父亲的情况,在那个年代,虽然他和父亲都身在高位,但是政治空气是非常紧张的,他们也都害怕在某一天会突然间被打倒,所以说话也很谨慎。当然,回忆起井冈山和父亲的相识,他和谭阿姨都笑了。
中午吃饭的时间到了,谭甫仁叫上他的老伴儿和我一起吃饭,老两口不停地和我叙旧,还回忆起父亲的一些轶事。我在等待着一顿美味午餐,但是军区政委的家宴也很普通,除去主食云南过桥米线外,还有三四个菜,也没有多少我梦寐以求的肉,不过我已经很知足了。
(4)父亲说,早知道谭甫仁死的这么惨,不如留下他
几个月后,我们非常震惊地得知,谭甫仁夫妇双双死于非命。由于我当时不在北京,所以不知道父亲闻知后的感受,我估计他将是很难过的,毕竟是艰苦年代一同走过来,共事又这么久远。
后来听妹妹陈小琴回忆,出事后父亲在电话中听到这个事件,很焦急地说:“赶快送医院抢救!”我特别记得那次在谭叔叔家吃完饭的一个插曲,我向谭叔叔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从1968年到1970年,我还没有和家里通过电话,想在他家打个长途给父亲。谭叔叔当即让秘书把我带到一个军区机关打了长途,父亲先是埋怨我不要给人家添麻烦,同时让我转告,一定让谭叔叔多保重。父亲的含义与其说是身体的告诫,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告诫,那个年代的政治空气太险恶了。
几年后,谭甫仁的一个儿子曾经到北京找过父亲,父亲见到他的儿子很难过。事过多年,父亲谈到这件事还感慨万端。父亲特别说,早知道这样,应该向中央打报告,千方百计地把他留在工程兵,那也就不会夫妇二人惨遭杀害了。当然,即使打报告也阻挡不住,因为谭甫仁将军从工程兵到云南是毛主席亲自点将,那是谁也不可能提出异议的。
父亲说,1968年中央把谭甫仁从工程兵调到云南,大家都没有准备,连谭甫仁本人也是突然间接到命令的。
云南当时是“文革”的重灾区,而且难以控制,武斗也在不断升级,这种武斗来源于江青的指示“文攻武卫”,文革初期江青还不像后期那样臭,很多人认为她的讲话精神很大程度代表了毛主席,所以纷纷拿起武器互相攻击。造反派由枪战发展到炮战,甚至把军工企业研究试制的尚处于在保密阶段的新式武器,也抢来用于武斗。
这一切传到北京,中央迅即采取措施,当时真正着急的是周总理,因为他要不仅要管“革命”,更要管生产,而后者才是最难的。周总理多次针对云南情况,作了指示。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便是一项重要举措。中央紧急开办云南学习班,本来和父亲共事的谭甫仁进入决策层视野,也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父亲说,他得知谭甫仁要离开工程兵真有点舍不得,但是谁也阻拦不了,这是毛主席点的将。
1968年1月24日,谭甫仁走进了乱哄哄的“云南班”。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当时还有“林副主席”)委托,谭甫仁以“学习班”办公室主任的身份主持了“云南班”的开学典礼并作了重要讲话。
2月11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各省和军队办学习班的情况汇报,周恩来首先谈了“云南班”的情况,当云南已来了八百多人时,毛主席大手一挥,摇头说:“不行,800人少了,要增加一倍。”
(5)毛泽东让谭甫仁做云南王
那天后半夜,谭甫仁突然接到通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紧急约见他。谭甫仁兴奋、紧张和不安地走进去。文革年代,即便高级将领也很少能够见到毛主席,更不要说和毛主席谈话了。毛主席向来是夜间工作,和下级见面也从来不拘一格,谭甫仁为之一惊,因为主席披着一件睡衣。谭甫仁还是很紧张,那个年代人们已经把毛主席视为“神”。
毛泽东的确有非凡的人格魅力,他首先讲起了云南的历史,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谈起来也深入浅出。毛泽东向来是个古为今用的大师,那个年代历史是个禁区,谁也不敢涉足:如果说哪个皇帝有作为,就是美化封建统治者;如果说哪个皇上是个昏君,就是借古讽今,影射毛主席,罪过就更大。全中国也唯有毛泽东可以随意阐释历史。
毛泽东谈到了吴三桂做平西王、永镇云南,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教训。最后,毛主席跃过数百年历史,转入正题道:“你要做平西王了,执掌云南边地,封疆大吏哟!”谭甫仁几乎插不上话,因为听毛泽东讲话是何等的荣誉啊,况且一个农民出身的将军怎么能同如此渊博的毛泽东对上话呢!
毛主席向谭甫仁传递了中央的想法:“中央已决定你担任昆明军区政委,名已正,言已顺,把云南班、昆明班办好,积累的问题解决掉,卸掉了包袱,再回云南。”
谭甫仁出了中南海,顿时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他走前对父亲说:“咱们从井冈山就在一起,在工程兵和你共事也很踏实,但是到云南就有点没底,如果你一起去就好了。”父亲也用那个时代的流行语言说:“这是主席对你的信任啊!”
1968年5月1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委谭甫仁担任昆明军区政委。6月17日,中共中央又批准谭甫仁担任昆明军区党委书记。由于要在北京办好两个班,故推迟上任。
6月底的一天,周总理又在中南海约见了他,再次对云南问题作了指示。从此谭甫仁正式主持云南全面工作。1968年8月11日,谭甫仁和“云南班”的代表们分乘4架伊尔18飞机,从北京抵昆明,正式当起了“云南王”,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关于谭甫仁的死,社会上流传的非常离奇,但是做为陈士榘的家属,当时就知道都是编造的故事。
谭甫仁离开人世是1970年12月17日,林彪在文都尔汗折戟沉沙是1971年9月13日,相距仅有几个月。而谭甫仁从井冈山时代就与林彪共过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冲击也不大,所以很多人都把二人联系起来。当时的新闻是全封闭的,民间一点不知道谭甫仁的死因,由于把事情捂的过死,所以谣传也就更厉害。
(6)传说谭甫仁奉林彪之命打周总理飞机是民间编纂的版本
流传在全国最广泛的一个版本是谭甫仁受林彪之名要打周恩来飞机:那是谭甫仁死前几天,云南王谭甫仁突然接到北京密电,指示谭甫仁在某月某日,将有一架从缅甸飞来的民航机,该机经过昆明时,务必击毁之。说他是云南王,是因为他担任着云南最主要的几个位置:中共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接到这个命令忐忑不安,因为不明不白地打下一架民航飞机有悖常理。而上级命令又不能公开违反,于是采取了退一步的战略,命令四架战斗机拦截迫降从缅甸飞向昆明的民航客机。
守候在机场的谭甫仁也在指挥着下一步行动。飞机下降后出来一个人,询问是怎么回事。谭甫仁走到悬梯旁,跟着走出来一个气宇轩昂、风度翩翩的老人,谭甫仁一见腿都软了,差点没有跪下,说:“总理好!”周恩来愤怒地说:“你们怎么还迫降我的飞机?是谁让你们这样干的?”
谭甫仁吓得不知说什么好,周恩来说:“马上向中央写报告,把这件事情交待清楚!”谭甫仁彻夜不眠,他在灯下写检查,怎样把事情交代清楚。他深知已经被卷到政治斗争的最中心,如果交代不清,不仅要犯罪,还要顶上谋害周总理这个遗臭万年的罪名,他也庆幸自己没有下令打下飞机,如果那样真是死有余辜了。
凌晨,谭甫仁和他的夫人竟然离奇地在昆明军区大院警卫森严的住所内,被一个手持双枪军人在卧室内连开五枪击毙,那是林彪的死党杀人灭口。
这真是一个如同惊险电影一样的版本,如果拍出来肯定比一些程式化的领袖人物的电影好看得多,但是这仅仅是民间杜撰的一个离奇故事。如果对真实的信息封锁的过死,民间的流传就会甚嚣尘上。
父亲事后谈起谭甫仁的死说过,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很多偶然凑在一起了。父亲说:“我也是司令员,如果大院里有个人要害我,也很难预防。外面的人想进来有难度,但是院子里的人要开枪,那就防不胜防了。”
真实情况是,1970年12月17日凌晨,地处闹市区的原昆明军区大院42号院内,接连发生了断断续续的几声枪响。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党的高级将领被暗杀的恶性事件在这个院子里发生了!最早知道的凶杀事件的是党办秘书邹贤玉,他马上告诉谭甫仁的秘书王克学。
我去过谭甫仁叔叔家,那是一个典型的军队高级干部经常住的小楼,我很难想象这个有着高墙围绕、幽静和保卫严密、总有警卫站岗的小院怎么会有人进去开枪杀人呢。从我记事起,我就是在这种格局的小楼居住的,一般都是一层住家属和会客,二楼是首长办公。楼的前面都是空地和草坪。和我家的司令小楼不同,我家的是解放初期盖起的,而谭这一座是解放后公私合营充公的大资本家杨希辰的小别墅。
谭甫仁的秘书王克学看见首长浑身是血,两只无神的眼睛向上翻着,谭甫仁的夫人王里岩更是毫无声息。王克学顿时惊呆了,也深感这将是一起会惊动毛主席、党中央的惊天大案。他本能地大喊警卫员”小李、小李!”但静悄悄的毫无动静。王秘书跑到警卫室,两个年轻战士正呼呼睡大觉,王秘书气愤地大喊:”你们怎么睡得像头猪,快给我起来!”
不久,警卫员小李从厕所哆哆嗦嗦地出来,原来这个军人竟然被枪声吓的躲进厕所。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中尽管调门很高,毛主席倡导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尽管在民间耳熟能详,但是由于一切秩序被打乱,一切规章制度被取消,结果会在军区核心的地方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事件。
(7)一个狗急跳墙的军区干部制造了惊天大案
谭甫仁和夫人王里岩被火速送往昆明军区总医院,王里岩两眉间中了一弹,正是要害部位。医生说:”看来已经死去一段时间了。”也就是当场身亡。谭甫仁身中两弹,一弹击中腹部,一弹打在头上。入院时,几乎没有血压。后来经过抢救才有了点微弱心跳。
在出事的第一时间,昆明军区副政委周兴命王克学记录,自己通过一号台要了周总理的电话,当时被文化大革命弄得身心疲惫的周总理在半夜尚未休息,周总理听到后也大为吃惊,当即指示:”要火速组织抢救;案子很可能是内部人干的,要抓紧时间破案,重点是军区机关内部;成立专案组,由周兴同志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
接到命令,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鲁维善教授飞抵昆明,在这之前由于谭甫仁腹腔内积满了血,医生只得剖开腹腔放出积血。后又打开胸腔,采用心脏按摩,但无力回天。午后4时,谭甫仁终因伤势过重离开了人世,那一年他正好是花甲之年。
当鲁维善教授到达昆明的时候,谭甫仁的遗体已经盖上了白单子,不过鲁维善教授肯定了昆明军区总医院的抢救方案是正确的。谭甫仁这位从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开国将军竟然倒在了自家院中的暗杀黑枪之下。
父亲后来总结这个案件时也说过,不管怎么说,昆明军区的保卫工作还是有问题,对这类突发事件反应太迟缓,尤其不能让凶手在杀了谭甫仁后还有机会开枪杀人。在和平年代久了,已经失去战争年代的警惕。
事情发生后,根据总理指示,昆明军区常委会开始抓紧破案。常委们至少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军人,面对这起在军区首脑机关发生的恶性案件也感到从无先例。最后,主持会议的周兴感到先把枪的来源搞清,在军区大院里查枪、验枪;要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哪怕是蛛丝马迹;会议当即成立”017专案组”,也就是”谭甫仁、王里岩被害案侦破小组”,由周兴任组长、蔡顺礼、王必成任副组长。
专案组经过初步调查,首先在现场获取了4颗59式军用手枪子弹壳。随即,军区负责验枪工作的保卫部发现两支59式手枪及20发子丢失。另外,发现现场的证据有墙根边皮革纸盒上,凶手留下了清晰的解放鞋鞋印,谭甫仁夫人王里岩倒的门框上有凶手的指印。
但是距离破案还有相当距离,因为尚没有嫌疑人浮现。这个案子后来的突破性进展竟然来自一个13岁的小男孩儿。因为这个叫王自正的凶手于谭甫仁被害后曾经出现过,王自正杀害谭甫仁后,还想杀死直接审查他的昆明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陈汉中。他想敲开陈汉中家的门,开门的却是这个姓马的小孩儿,他在睡意朦胧中告诉王自正在另一个门。
王自正知道走错了门,他直接敲陈汉中的门,无人答应。恰巧陈汉中出差,躲过一劫,但是这个小男孩儿已经记住凌晨5点来的这个大人是同院小朋友王冬昆的爸爸。文革中讲究”人民战争”,在发动广大群众破案方面有其优势,当然这种方法也”误伤”过很多人。其实这个名叫王自正的嫌疑人本来已经处于被审查的境地,做为军区保卫部的一名干部保密员,他不久前平职调到云南文山军分区政治部担任保卫科科长。但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审查出有重大历史问题没有上任就被停职反省,拘押在昆明市西坝原军区联络部俘虏管理所接受审查,由保卫部陈汉中科长负责调查。
(8)凶手之谜
但是王自正一直否认自己杀过人。自从13岁小男孩儿发现他那一晚出现外,人们还回忆起在案发后王自正鬼鬼祟祟,犹如惊弓之鸟。但当别人以惋惜的口吻谈起谭甫仁被害的消息时,他却流露出一种暗自窃喜的神态。还有专案人员带着13岁小男孩儿在院里出现的时候,他曾经忍不住哭了,还喃喃自语:“见不到老婆孩子了!”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荷枪实弹地采取紧急特殊的行动,但是有关部门依然没有对这个凶残之极的杀人魔王有足够的警惕。1970年12月31日晚10时,专案组命令陈汉中、李伯志去王自正的隔离室进行审问。王自正心事忡忡地躺在床上,由于都是同事,陈汉中对王自正并不严厉,:“起来,到饭堂来一下,有点事。”
王自正知道末日来临,他表面上顺从地起床和穿上衣服,心中却在筹划着垂死的挣扎。他问陈汉中:”穿哪双鞋子?”陈汉中严肃地告诉他:”穿那双解放鞋。”王自正更知道完了,因为枪杀谭甫仁的时候他就是穿的解放鞋。王自正穿上鞋,然后弯腰系鞋带。王自正系完鞋带后,敏捷地从被窝摸出一支59式手枪,甩手就是两枪。
李伯志被击中腹部,倒在地上,陈汉中被擦伤右手。杀红了眼的王自正则提着枪夺门狂逃。幸而这次警卫班的战士警惕性很高,立即包围过来。王自正自插翅难逃,抓住也是必死无疑,便举枪向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他的脑浆飞溅,王自正终于见了阎王。
父亲也说过,凭我们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军人的经验,不该有这样惨重的损失,其实这种对垒在战争中是一个很小的交锋,如果头脑像战争年代那样清醒,可以把损失见小许多。
凶手的最大特点无非就是一个亡命徒。凶手王自正原名王志政,河南内黄人,富农出身。做为一个现役军人――那个年代军人的地位至高无上,尤其在非常讲究出身的年代还能留在军队里,应该很知足。
王自正的为什么要采取这么极端的方式呢?在他暗杀谭甫仁之前,调查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进攻中原后,其堂兄带领一个还乡团对王自正老家的村庄反攻倒算,枪杀了村武委会主任,王自正参与了这次反攻倒算的杀人行动。后来他本人逃往他乡,由王志政改名为王自正,到起它地方参加了解放军。文革当中清理阶级队伍,把问题扩大化乃至冤假错案也不少,王自正在解放前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也许永远是个谜。1970年初,他被提升为昆明军区政治部保卫科长,他还没有来得及弹冠相庆,便因家乡告发历史问题而被送到俘管所隔离审查。
那个年代无论是真的还是被冤枉的,都采取坐以待毙的态度。王自正是个极少的另类,他决心鱼死网破。他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我不能这样死;我要死,也要杀几个人。”“能报复的,只有这一条。”
王自正在笔记中列下了好几个要杀害的人的名字,包括军区副司令员陈康、鲁瑞林、田维扬等人。权衡之后他又写道:”不如杀谭甫仁,影响更大,发泄心头之恨。”“但没有枪,要设法搞到枪。”“拿到枪半胜,见到人全胜。”这个隐藏在昆明军区心脏地带的杀人狂魔竟然能够偷出两支手枪,而且进入了谭甫仁壁垒森严的住宅。可见那个年代虽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但是打乱的规章制度也留下了各种隐患。
(9)几个偶然的疏忽造就了共和国最大的凶杀案
谭甫仁的住宅共布设了五个警卫员,前门二人,后边三人。那时候正值“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和苏联打仗,部队正搞所谓“千里野营拉练”。但是再拉练也不能影响首长的安保,可是谭甫仁的警卫员也被拉去,警卫员仅仅剩下了两人,这给凶犯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当然一个突发事件也有偶然因素,凶犯独立作案其实并不容易,他深夜跳进谭甫仁的深宅大院和高大的围墙,就是从食堂拿了一张凳子。食堂原来养了一只狗,如果狗在肯定会和他撕扯,他也不会有机会,偏偏凶犯做案前一两天狗失踪了。
那一晚,王自正就是从厨房穿过天井进入小楼的。凶手对谭甫仁的住所早有了解,他直奔谭居住的卧室。因为年龄大,谭甫仁夫妇又喜欢安静,他们有时不同居一室。凶手敲门,谭甫仁夫人王里岩以为是谭甫仁敲门。王自正面露凶光地问:”谭甫仁在什么地方?”王里岩知道不好,她尽力保护丈夫:”不知道。”
凶手进门搜寻,谭果然不在,王里岩呵斥:“你要干什么!”凶手用手枪对准司令员夫人,王里岩本能地跑到沙发旁,她已经被这个场面吓得无力反抗。王自正顶住王里岩的额头扣动扳机,子弹从司令员夫人额心穿过,夫人当场死亡。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王里岩为了保护丈夫,曾经死死抱住凶手,并高喊:“老谭快跑!”由于当事人都已经死去,所以永远无法判断那种说法更准确。由于射击距离过近,谭甫仁夫人弹洞四周的皮肤已被枪口喷出的气体灼焦。
这一刻是在1970年12月17日凌晨4点多,枪声本来已经划破寂静的夜空,但是久远的和平年代已经让人麻痹了也让人惊惶了。其中一个警卫员吓得不敢出来,另一个警卫员发生了非常荒唐的事情,这位年轻战士正和一个比他大30岁的保姆在一间屋里姘居。据说这位风韵犹存的女人是国民党军官的太太,老公解放前夕跑到了台湾,20多年一直独身。对于生理的需求也是人之常情,她眼中的小战士也成了猎物,徐娘半老的她想啃嫩草,小战士怎么禁得住诱惑,从未尝受过男欢女爱的他已经晕菜了。
偏偏这个老保姆在谭甫仁家一个人烧饭洗衣做杂物,又为凶犯的得逞增加了成功的因素。那一刻,身经百战的谭甫仁也发生了判断上的错误,听见枪声他本应躲在屋里,因为他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人,只要他不死,都不是什么惊天大案,谭甫仁偏偏跑了出来,跑出来的时候也没有带上武器,因为多年来司令员已经不用亲自带武器了。
同一时刻住在他家另一个房间的六姨妹也惊惶失措地跑了出来。凶手并没有理睬六姨妹,径直指向谭甫仁。谭甫仁跑到窄窄的小天井里,已经被挤在无处藏身的空间,王自正看准了谭甫仁进行射击。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用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方式死在一个亡命徒手中。
王自正的确是个凶残无比的家伙,但是如今回顾起这个事件,也有值得思考之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阶级斗争无疑被大大地扩大了,即使犯罪嫌疑人真的有什么问题,也不是在法制化的轨道上进行,而是踏上亿万只脚、大肆侮辱人格、永世不得翻身和极力株连九族。当时很多人都默默地承受了,但是也有人会走向极端。
(10)父亲说:谭甫仁死于错误的文化大革命
谭甫仁做为云南最高的领导者,也要忠实执行“阶级斗争天天讲”的路线,如果他放松了,他马上会被赶下台。为了不落后和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谭甫仁来云南的一件大事就是“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追查明显是极左分子杜撰出来的“滇西挺进纵队”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做为一个老军人,谭甫仁和父亲一样,总怕阶级敌人“变天”“复辟”,因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有多少战友牺牲在战场,革命的成功是多少人头和鲜血换来的,可是他们明显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无法逾越时代的误区,不把经济建设做为中心而把“阶级斗争”一再推向白热化。
在这方面,谭甫仁在这方面比父亲“左”,为写这本书,我采访了几位在工程兵司令部工作过的老同志于香林、李柱江,他们对我说“陈司令和谭政委都是好人,但是陈司令在那个混乱的年代还懂得政策,比如有个干部文革初期曾经到北大、清华看大字报,也有过造反行动,有人主张开除党籍和军籍,谭政委同意了,并且说应该开除。也不能说谭甫仁爱整人,他怕犯立场错误。你父亲却说,他作为知识分子敏感一些,看看大字报,造造反,也没有太多的错误,不能轻率地开除一个人。这个人就被你父亲保住了。”
他们还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工程兵三支两军,发生过造反派冲击军队的事情,工程兵领导讨论,谭甫仁就主张采取强硬措施。陈士榘司令员却说,我们不能做千古罪人!后来两个人还争论,陈士榘说,咱们就按总理最近的指示,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听两位老同志的回忆,我才知道父亲作为一个军人在这种大是大非上头脑还是清醒的。
谭甫仁做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在云南的行动是符合当时的潮流的,他指导当地各级领导:“(阶级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你们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我在个旧地区讲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了九百九十多个坏人。有人问,可不可以拉出去游街?游街后能不能把这些人下放劳动?我说游街可以,下放劳动也可以,戴白袖套也可以,让群众识别嘛!”
根据有关统计,云南仅下关市一地,追查“滇挺”分子运动中就打死逼死七百多人,打伤致残一千多人。据云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统计,曲靖和昭通地区,受“滇东北游击军”假案牵连的干部群众多达六十万人,仅曲靖就有二十九万三千一百九十三人,其中二万多人被批斗,二千多人被关押,四千多人被打伤,二千多人被打残,二百多人被逼死,一百多人被打死……
谭甫仁人生终点无疑是悲惨的,他和父亲一样,一直在追逐着一个美好的理想,并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但是舵手的失误、时代的局限、文化的制约,都让他们承担了一个尴尬的角色。我父亲晚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这一点,他对我说过:“一条正确的路线引导谭甫仁成为我军的一名高级将领,而一场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又导致谭甫仁遭到如此悲惨的下场!”这位起步于革命圣地井冈山的将领被错误路线送进了天国。
对待父亲和谭甫仁,都应该有个更准确的评价,既要肯定他们为民族解放立下的功绩,也要思考他们为什么会做为一个群体那样毫不怀疑、不能诘问地参加那场历史闹剧。几十年过去,我再不把这种失误归咎于觉悟甚至道德。就是很多从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的老干部,如果文革重用他们,他们会自觉的抵制吗?
我想任何经历过这场运动的人都会找到答案。
愿历史能够原谅他们,也希望历史能够认真总结他们。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