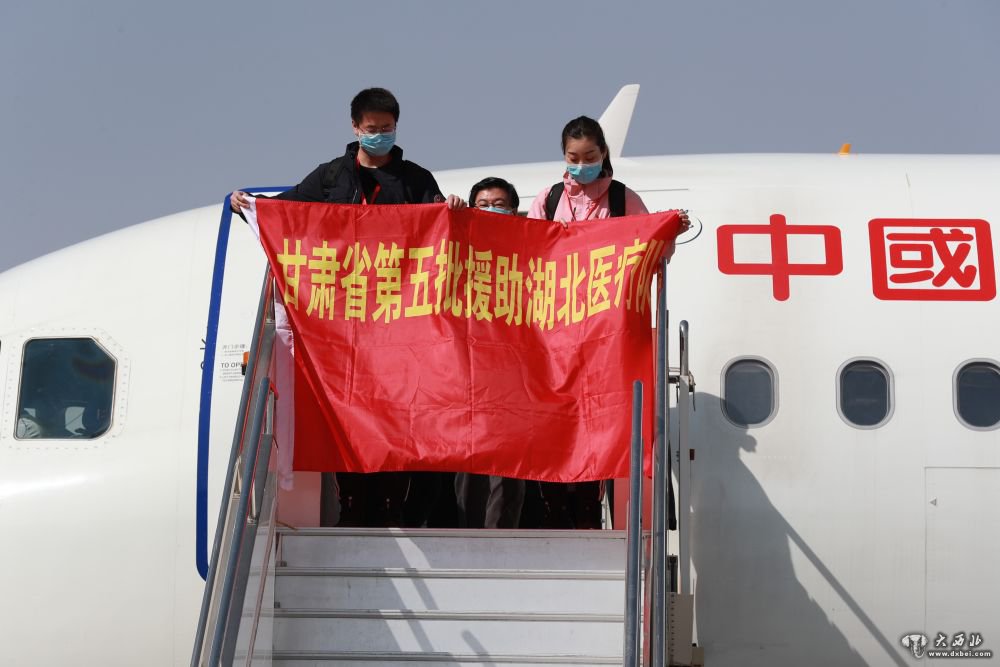1964年,我在一个劳改农场改造,第一次见到那天性驯良,美如天使的水禽动物,是在劳改队大队部的葡萄架下。我隔着铁丝网,神往地望着白天鹅那一身洁白的羽翼,心里不禁自问:蓝天才是它们的故乡,江河湖泊才是它们的天堂,它们到这儿来干什么?还摆出一副悠然自得、闲庭信步的架势!飞吧!我的天使!这儿是囚笼,不该是你漫步的地方,露珠闪光,水草凄迷的青青河畔,那儿有你的群落,有你的家族,为什么你要眷恋这个鬼地方呢?
后来,我知道了:原来这两只天鹅是被主人剪去了一圈欲飞翅膀的羽毛。它们来自天苍苍野茫茫的东北大草甸子-兴凯湖,那儿的劳改农场捕获了它们,场长从兴凯湖调往我们所在的劳改农场时,把这“姊妹俩”也装进囚笼,像携带仆从眷属那般,把它们迁移到这个地盘上来了。
使我忧虑的是,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它们天性*中的善良,被岁月的流光啮食掉了,使这天使般的两姊妹,只剩下天鹅的形态与仪表。有一次,我到劳改队办公室去请示什么事情,当我穿过葡萄架时,那“两姊妹”竟然拍打着仅存的短短的翅膀,对我发动了突然袭击。
一只对我嘎嘎狂叫,神态犹如家狗般凶厉。
一只用嘴叼住我褴褛的衣袖,撕扯下我袖口的一缕布条。
我挣扎着,我奔跑着,待我逃出葡萄架,惊魂初定之后,留给我的是满腹的狐疑:
“这还是天鹅吗?”
“这是两条腿的狗?”
“这不是黑狗、灰狗、黄狗。”
“这是被异化了长着翅膀的白狗!”
1950年代中期,当我还是个青年作家的时候,我去过东北三江草原。那儿块块沼泽,如同大翡翠中镶嵌着的一块块宝石,它们在那野花盛开的水泊旁,交颈而亲,合翼而眠。那姿态像是无数下凡的安琪儿入梦。在这美丽的群落中,总有一个“哨兵”站岗,它们警惕人类,它们警惕枪口,它们警惕秃鹰,它们警惕野兽。它们从不惊扰邻居,它们从不吞噬同类,它们从不以鸟类王国王后自居,它们从不趾高气扬,自喻为“羊群中的骆驼”.
据萝北草原的一个猎人告诉我,他从不捕杀白天鹅。他说此种鸟类不仅羽毛如雪,还有代其他鸟类孵化雏鸟的本能。有的“娘”把娃儿生下来后,一扑棱翅膀飞了。白天鹅则扮演“娘”的角色*,把其他鸟类家族的后代孵化出来。群居草原和与囚徒为伍的白天鹅,反差如此之大,简直令人吃惊!
仔细想想,似乎从中发现了一点儿道理。地壳喷出炽热的岩浆可以造山,磨盘眼里流出的粮食可以碾成面粉,美丽的天使安琪儿,在主人驯化豢养以及囚徒们的挑逗凌辱之下,就不能改变它那颗善良的灵魂吗?它最初是出于生存本能的反抗,久而久之就把人类视若顽敌,见了脖子上驮着脑袋的人,就首先对其进行袭击!
大约过了年把光景,一群白天鹅在春日北返,它们在天空中发现了两个同族,在天空徘徊良久之后,终于有两只飞落下来,大概是想来叙叙手足之情,但它们刚刚落地,两只在囚笼旁生活的天鹅,则像凶神一般,与来看望它们的两只天鹅,摆出武斗架势。飞下来的天鹅鸣叫着说着天鹅家族才懂的语言,但这两只“地鹅”,则已完全丧失了天鹅家族的一切属性*,将飞来的兄弟姐妹,叼下来一团团白色*的绒毛。飞来的两只白天鹅历经惊愕之后,终于起飞了。但这时猎枪响了,这对来探望家族兄弟的美丽天使,双双从天空中坠落下来!
枪声惊醒了我的梦,于是我想起了文学的使命。
善与恶。
生与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