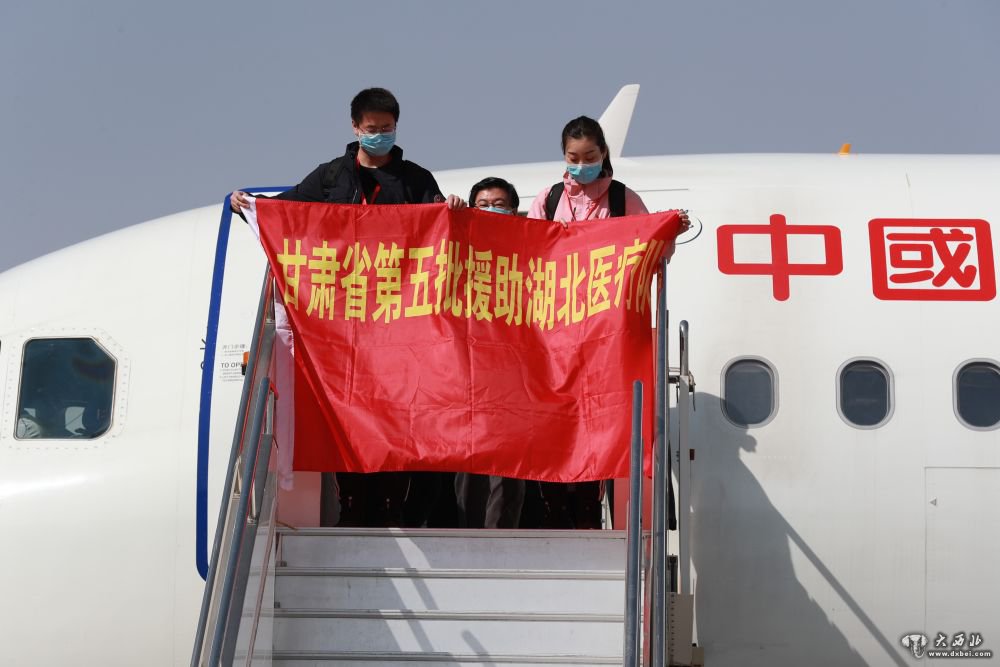他们开始唱诗的时候,屋子里还非常昏暗。
几十人围坐在一铺大炕上,微微地垂着苍黑的头颅,把目光放牧在手中的小本子上,嘴唇敦厚地嚅动着,仿佛每个小本子都是一片蜂飞蝶舞的草原。
坐在炕头领唱的是西林小教堂的教长温成大婶。温成大婶的天庭极其饱满,象一块银色的瓦当一样,泛着一层古老而圣洁的光泽。
他们是从早晨八点钟的时候就开始唱诗的。那时东方已经出现了一些紫红的颜色 ,太阳刚刚升起,黑褐色的森林顿时穿上了一件灿烂的霞披,远远一望,象一艘行驶在白雾轻扬的海上的红帆船。
可是,等到他们唱的时候,冉冉升起的太阳就被一大片浓重的乌云裹住了。辉煌的光线顿时从地平线上消失,森林也恢复了苍劲的古铜色。
孙大娘和马凤兰来得晚了点,炕上的人基本坐满,只有炕梢还亮着一小块空地,所以两个人就肩并肩地挤靠在一起,根本看不出是一对昔日因为烧荒占地而打得不可开交的仇人。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崇你的名,
愿你在地上掌权,
愿你的旨意实现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一样。
炉膛里烧着文火,没有声响,因而屋子里只有微微的暖意。教堂的空地上堆着喂牲口的干草,干草瑟瑟抽动的时候,你会发现机灵的毛茸茸的小老鼠从那上面窜过。
我的姨姥坐在第一排正中,唱得泪水婆娑的。这是一个从早到晚说的话足足可以装一个车皮的老太婆。她今年六十八岁了,人很干练。早晨起来时,我就见她梳着油晃晃的疙瘩鬏,穿一件灰色大襟衣裳,在用鸡毛掸子扫尘。我知道她要去做礼拜,我想去看看,在四姨的帮助下苦苦央求了一刻钟,她才不情愿地说:
“你去归去,可是不能乱说话。”
太阳的生命力毕竟是强壮的。不久,那片包裹着太阳飞轮般肉体的乌云被它的灼人的光辉给击碎了。阴云象败兵一样仓惶逃窜,天空霎时象再嫁寡妇的脸一样明朗起来。
白炽的阳光透过昏黄的玻璃窗,给刚才黯淡的屋子弥漫了一大片灿烂的亮色。好象一盏奄奄欲熄的油灯忽然被注入了大量芬芳的油,在一阵痉挛中蓬勃地亮堂起来了。
那些唱诗的头颅也就一下子光辉起来,好象秋天果园中一大片成熟的蜜桔,在炫目的太阳下泛着光泽。
自从我家搬出西林,我便很少回村子了。只是每年的清明和春节前夕,才务必要赶来为父亲上坟。
上次清明来时,细雨纷纷,大山刚刚露出一丝朦胧的绿的微笑。到四姨家时,见姨姥躺在炕上,双目无光 ,干瘦如柴,完全是个等待下葬的人了。姨姥见了我,便说她活到寿数了,把人间所有的苦处都尝遍,该走了。惹得一家人都跟着掉泪。
可这次来,姨姥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长途汽车到西林时,正是傍晚,天上弥漫着小清雪,西林村所有的房屋都被包容在白蒙蒙的雪雾中。
来接我的不是四姨,而是姨姥!
她穿着一件青布棉袄,围一条驼色的拉毛长围巾,我认出那是四姨去年戴过的。
“你四姨说车三点多钟到,等等等,等到现在才来。”
她一接过我的旅行袋,就开始喋喋不休:
“你妈身子好吗?你弟不淘气了吧?”
“走到半路就下雪,路滑,车开得慢,就晚点了。”我说。
汽车站离四姨家不远。姨姥背着我的旅行袋,步子还迈得很有气派,她显然发了福,先前脸上深深的皱纹浅显多了,而且声音也愈发高昂,节奏极快,好象是在喷射一串串的子弹。
晚饭后姨姥就回她的小屋去了。四姨夫正对着一副破旧的滑雪板发愁,因为他准备在假日去山上打猎。四姨还是改不了早睡的习惯,已经裹着一床厚被在炕头上舒舒服服地躺下了。而我的两个小表弟,正在他们鸽子笼一样的小房间里玩着我带给他们的积木,不时地因为建筑方式不一致而吵嘴。
我洗漱完毕,准备上炕睡觉。奔波一天,也感觉到疲劳了。
照理说,我应该跟姨姥住一个屋子 ,让四姨和四姨夫住一处。可是,四姨和四姨夫多年来感情一直不合谐,但也不吵嘴,所以我每次来,四姨都要求我跟她住一起,把四姨夫打发到姨姥的屋子去。
还没上炕,便听到姨姥的房间传来一阵虔诚的祷告声。我寻过去,发现她正端坐在炕沿,对着一个小本子念着:
一天工作做完毕,关上门来守安息。天石天军站着岗,耶稣就在我房里。铺铺被,我就躺在主的怀里睡。主耶稣赐恩典,保我一夜得平安。唱个灵歌养养神,耶稣不叫我胡想。我要睡觉合上眼,耶稣领我上天堂。
我“扑哧”一声笑了:“姨姥,您信耶稣了?”
她受了一惊,本子掉到地上,很不满意地看了我一眼,说:
“我信神,不信神是不行的。信神后,孙大娘家的猪崽子一天就卖掉十个,揣回来响铮铮的三百来块,乐坏了一家人;马凤兰也不象过去那样爱骂她男人了,她家的牛不但越长越招人稀罕,而且前天圈 里又独独多了一头大牛,粗腿、圆肚、大头,从牙上看年岁不大,一问,不是咱西林村的物,你看神不神?”
“那也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说。
“神牛,”姨姥反复地说,“神牛,神牛。”
温成大婶的左眼炯炯有神,右眼则大而空洞,黯然无光。她的右眼是今春上山伐树时被一棵小树丫戳瞎的。阳光前进到她右眼时,就偃旗息鼓,好象一队身穿军服的将士,走到了绝望的峡谷边缘。
我长这么大,在西林村,还是第一次听到由这么多人合唱的歌声。
这是一种柔婉、绵长、韵味深沉的歌声。它象农家除夕的饺子一样,带给了这些疲惫辛劳为生活奔波的人们无限幸福。
西林小教堂是我见过的教堂中最简朴、最别致、最有风格,同时也是最古怪的一座。
它诞生的历史还不到七个月,但是作为房屋的存在,却已经八年之久了。
这是教长温成大婶的一爿豆腐店。除北墙是砖的外,其余的都是土坯垒成的。房子跨度不大,由于年久失修,东边山墙的柱脚已经半朽,因而西面象船头一样翘着,而东面则象重载的货轮一样深深地吃进地里。房子的四围,是一大片草场。春季的时候蜜蜂都跑到那里找花粉吃,而一到了盛夏,温存的草长得茂密时,不只是些小动物,就是那些厌倦了炕头生活的人,也愿意钻到那里制造出一些风流韵事来。
当然,这不是冬天的话题。
此时的太阳已经不象初升时那么羞答答的了,先前堆在天边的那些绯红的颜色已经消失。因而阳光象过了门的小媳妇一样泼辣起来,山上的白雪被它映照得更加灿烂。
我看见温成大婶打着手势在教一首新歌,唱诗的人象一片向日葵微微仰起了头。姨姥在仰头的时候用手绢擦净了漂泊在眼角的泪花。
四姨说,自从姨姥信教后,姨姥饭量大增,一顿饭足足可以吃两个大馒头,还不算稀饭。而且屋里的活也全都包揽了,听说酸菜缸上压着的那块大青石就是她一个人从石头山上背回来的。
我知道,不到中午他们的礼拜是不会结束的。就一个人悄悄地出了小教堂,沿着被白雪覆盖着的草场到马凤兰家去看那头“神牛”.
“神牛”果然与众不同。当马凤兰的丈夫把我带到牛圈时,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如姨姥所说的肚圆、腿粗、大头的牤牛。
它健壮英俊得像一个成年男人,仿佛拉一天的犁杖下来也不会疲惫。它的眼睛象日光下的雪山那么迷人,毛发是浅棕色,即使在暗处也明显地看出了那上面的光泽。
“它就是自己来的?”我问马凤兰的丈夫老赖。
“你不信?它真是自己来的。”老赖有点缺心眼,豁着一口的牙,白白唬唬地跟我说:
“那天清早我一靠近牛栏,刚把草料倒在槽子中,就看见它了,当时还吓了我一跳!它的身上没套任何绳子,也不见伤,油光光的,我还当是谁家的牛走错了栏!可一想在西林这屯子里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牛呢。肯定是我屋里人信教感动了天老爷。”老赖说得唾沫星子四溅:
“我要骗你个小翠子呀,咋着?我老赖就是你孙子!”
我跟老赖整整是两代人,差一个辈份,他跟我个小姑娘赌这样的咒,实在有些荒唐。于是,我就顺水推舟的说:
“神牛便是神牛吧。”
老赖惊喜地翻翻眼珠,嘴角淌出一线口水。
过年杀鸡宰鹅的事历来是姨姥一个人的。可今年姨姥却坚决不干杀生的事了,而且也戒了烟酒。
四姨夫杀鸡就象砍柴一样,把脖子拧歪放在木墩上,举起菜刀“嚓”地一剁,鸡头就象一朵鲜秾欲滴的花垂落到地上。姨姥见着自然骂四姨夫一顿,而我的两个表弟则为四姨夫痛快淋漓的剁法而痛快、欢呼。
晚饭时,姨姥问我去过教堂后头痛病是否好了。我摇摇头,她就用筷子敲着我的碗沿,说我不诚心,什么病也不会好。四姨听了,皱了一下眉,但是没吱声。四姨夫捺不住性子,瓮声瓮气地说:
“那都是自己骗自己。”
“你不信,你就不信!你不能对神不恭敬,在我家里还没有出过这样的败类!”
“我就不相信所有的教徒都真信那个!”四姨夫不打算吃饭了,他的脸气成了猪肝色。
“你怎么敢红口白牙污人清白!”姨姥扯着嗓子上的几根老筋在吼。
“算了算了,有什么好争的。”四姨不满地插言。
“你就咒神吧,你再打猎时小心滑雪板弄折了你的腿!
”大腊月的,诅的什么咒!“四姨对姨姥的火气在升级了。
姨姥最近怕起四姨来了,因而四姨一动气,她也就不敢再吱声。四姨是西林村的党委书记,教堂的事多多少少要由她来掌管。现在姨姥他们这些教徒正在为能新建一个小教堂而奋斗。因为现在的小教堂已经摇摇欲坠。四姨完全可以出面向政府打个报告,请一批款来。
于是,我就马上变换个话题。我说明天是腊月二十三了,过小年,应该给父亲去上坟了。
谈到上坟,姨姥便叹气了。她说我爸爸死得早,就是因为喝酒的缘故。她说烧不烧纸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心意到了就行。我明白,她信教后,是不允许烧纸的,也就默不作声。但临睡前还是打了厚厚的一沓纸钱。
上坟须是上午日出之后。
第二天早起我发现灶台上放着三包用黄裱纸包的菜。有煎鱼块、炒鸡蛋,还有一个葱爆肉,都是父亲生前喜好的。姨姥背对着我,站在窗前望着外面单调的风景擦眼睛,我知道她在伤心落泪哩。
把烧纸和炒菜打点在一个竹篮子中,朝腕上一挎,我就去商店买酒了。
在大城市住得久了,你走进西林的小商店,会有一种恐惧心理。因为商店不大。顾客稀少,店面就显得冷清,连营业员也是无精打采的样子。一走进去,几双疲倦的眼睛就亮闪起来,很刺激地向你逼射来,给人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
”小翠,又是买酒给你爸上坟!“
”嗯,温成,拿瓶最好的。“
温成答应着,背过身到货架上取酒。温成还是那么瘦,半年不见,胡子更稠了。
”你也在读<圣经>?“我发现柜台上躺着一本《圣经》。
”我妈当教长,我自然也是半个唯心主义者了。他们说耶稣是个大医院,能治万国古怪病,我看看,我的病该怎么治?“
”你结婚就好了。“我低声告诉他。
他苦笑笑,把一瓶富裕老窖放在我面前,”拿去吧,你爸爸好歹教过我一回,也算是我尽弟子孝心。“
我知道推让下去就难免虚假,何况我和他之间还有过姻缘,所以也就不付钱,把酒放在竹篮中。
”今儿小年,你妈又在家忙着送灶王爷了吧?“
”她老人家一大早就拉着手推车去上山拣柴去了。“
”她不送灶王爷了?“
”送什么,她说只要信神,别的便都不用信了。“
以往到小年的那天,温成大婶送灶王爷,排场可是整个西林村的女人都张口结舌的。她不但要把供给灶王爷的东西做得全,摆得哪里都是,而且要把香火烧得旺,晚上祭灶的炮仗也独一无二地响得轰轰烈烈。
而今年,没有了这种情调,总觉得好象是吃了无盐的菜,不是滋味。
上坟回来,弥漫在清晨的冷雾消失了。天空蓝得透明,山雀飞得很潇洒。几只狗在小松树林的空地上刨雪玩。
路过马凤兰家的时候,我见老赖傻乎乎地提着一根牛绳,晃在大门口表演套牛的游戏。七、八个小孩子象熊猫一样圆滚滚地围着他,笑得咯咯的。老赖没戴棉帽子,耳朵冻得红红的,象两只公鸡冠子。
”你们家的神牛爱吃料么?“我问他。
”爱吃死了。“老赖嗬嗬地笑着,”吃得肚子胀得好象怀了三胎的婆娘!“
”赖货!“马凤兰提着脏水桶出来,浇了老赖一脚的湿。很快,老赖的鞋上结了一层薄冰,闪着很诱人的光。
老赖笑笑,拧了一把马凤兰的屁股,连连说着”睡觉去,睡觉去“.就光着响亮的秃头回去了。孩子们也象抢足了食的小猪一样,不慌不忙地走掉。
我突然发现四姨夫倚在马凤兰的柈子垛前,跟头大象一样,头垂得很沉,极象姨姥爷过世时他吊孝的样子。心中不觉”格登“一下,眼前闪现出马凤兰婚宴上四姨夫醉哭的情景。
西林村似乎谁都可以死去,但独独老赖不能死。因为他在人们心目中就是一支曲儿,酸曲儿也罢,甜曲儿也罢。
他穿开裆裤的时候就喜爱唱歌逗乐。他的现在睡在墓地的母亲,曾经为儿子的天分而自豪过。后来,他长到十八岁的时候,人们才发现他天性泼皮,刁顽不化。而且不知是因为他属牛的缘故,还是他的父亲曾经做过牛贩子的缘故,他对牛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我十一岁的那年 ,记得是一个凉爽的雾蒙蒙的早晨,忽然听见生产队的牲口棚里传来一阵吵闹声。等我慌慌张张趿上鞋子跑去看时,见老赖正被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给捆着揍。当时村子里如花似玉的马凤兰垂着一条蟒蛇样的粗辫子在哭,她的乌亮的头发上沾满了草料。
大人们讲,老赖早起放牛,看到马凤兰撅着屁股劈柴,就象小偷一样堵了她的嘴,抱她进了牲口棚的草堆上,跟她睡了觉。
那时我不理解为什么睡了一次觉就要把老赖打个半死不活,而且马凤兰要那么伤心地哭。但我记得西林村的人在痛打了老赖之后,马上又给他张罗喜事了。而且,那天的婚宴可以说是西林村有史以来最辉煌的一次,许多人都吃醉了酒,就连我的四姨夫那天也喝得东倒西歪,并且醉哭了。
晌饭过后,我就跟姨姥一起围着箩筐拣豆荚儿。外面开始阴起天来,并且起风了。四姨说恐怕要下大雪。我的两个上小学的表弟就欢呼起来。因为体育老师讲了,等着再下一场大雪之后,小教堂周围的地片草场就可以做为滑雪的训练基地。他们从来没有驾驭过滑雪板,因而对大雪的企盼就象企盼新年的棒棒糖一样。
果然,雪很快就来了,太阳遁得也快。天和地此刻都是灰蒙蒙的一大片。雪花开始下得很纤巧很秀气,后来雪片变得粗犷起来,鹅毛大雪便风靡了西林村和西林村以外的山峦原野。
小教堂周围的草场顷刻就变得丰满了。
豆儿没拣完,小脚的孙大娘哭声连天地找四姨来了。她说温成大婶上山时让树枝把那只好眼也给挑冒了,现在正一脸的血,什么也看不见了。她让四姨赶快给找个车去县城医院。
这样的大雪天,又逢小年,到哪去拦车?四姨一边骂着什么,一边喊四姨夫赶快套马爬犁抄近路送她下山。
可怎么也找不见四姨夫。听表弟讲,四姨夫晌饭后上完厕所,就背着一副崭新的滑雪板进山了。
”死熊!“四姨骂着四姨夫。
”死熊咧!“姨姥也哭着骂。
不知怎的,我的脑海里一下子洋溢起他们做礼拜的歌声来。仿佛那歌声每一个音符都在敲击着雪花的翅膀,在天地间发出一种花白而冷清的曲调。
”人不能太贪财,我太贪了,神又惩罚我了。“温成大婶很沉着地跟四姨讲:
”不用去治了,我什么都明白了。看在基督的面上,你请来些钱,盖个象样的教堂吧。“
喜闻放屁
肠胃科住院大楼513号病房里静悄悄。吊针的药液一滴滴坠落,仿佛可以听到声响,像人的脉音。
医生来了,什么也不做,只问您今天放屁了没有。
四个病号有三个做了肠胃手术,一个亟待医生下手。31号已经是第三次胃穿孔了,这一次大出血,刚刚急救过来。32号罹患直肠癌,做了根除手术。33号是一个农民,结肠癌,同样切除了一段肠子。下刀之前他很害怕,医生笑着安慰他,人的肠子有六七米长,我只切除你的10公分,担忧个啥?
现在捱过了一刀,33号又担心个屁!
他和32号同一天入手术室,人家第三天就顺利放屁了。那是一个阒寂的愁苦之夜,一种奇异、清晰的声音从32号病床发出,开始时断续而浑重,像大型拖拉机在发动,接住变得细长尖锐,当音调升到极点,好比布帛的迸裂,嘎然而止……
然而,等到第六天了,33号还是什么屁都没放一个。
32号躺在病床上欣慰地说:”放屁是肠胃手术成功的一个标记,放屁证明肠道通了,通了就可以进食,可以拉屎……“他这屁一放,护士马上把他身上的尿管、胃管全拔了,一下子无管(官)一身松。
33号黯然神伤。他的老婆回家借钱去了,住院半个月,刚好花了一万元,卖了两头牛、一头猪、三亩青椒。现在每天几百元的医药费,护士一次次来催,说再不交费就停药!催急了他就哭,说:”我还没放屁呢,屁一放我就走人!“
他遵照医生的嘱咐不断翻身、蠕动、深呼吸,折腾。平日响屁连发,臭气熏天,如今三脚都踹不出一个来。可知,一个人落到了”癌“这地田,还有什么屁用呢!
田里的水稻该灌溉了,西红柿该施肥了,他想回家,扛一把铁锄,在庄稼里四处转悠,赤脚踩在泥土和牛粪上,鼻子嗅着稻香……他一辈子守住这一块土地,辛勤劳作,自生自养,然而,天意弄人,竟要他绝。
医生来了,还是问这一句:您今天放屁了没有。他哭丧着脸,反问医生,是不是手术出了差错,肠子没有粘连上呢?医生也皱眉头,说病人有个体差异,再耐心等待吧……
他嗫嚅着说:”这里是高级宾馆呢,谁躺得起?!“
第七天,他老婆回来了,只借到800块钱,听说屁还没放,一转身就抹眼泪。
同这一天,32号的伤口拆了线,立即回家。
……
这是一个秋雨迷蒙的深夜,医院外的街灯昏黄,行人稀落,癌症患者农民33号”遁逃“出院。他一路躲过了值班的医生和护士,像做贼一样遛走。
做人要厚道!他常常这样说。然而,他今夜做了一件极不厚道的事--故意拖欠医院一千多块钱的医药费--非法出院!
他老婆挽扶着他赶路,边走边问,俺们屁还没放,肠子还没通,回家怎样拉屎啊?
他狡黠而惭愧地说:”屁有响与不响之分呢,我刚才放过了,是个不响之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