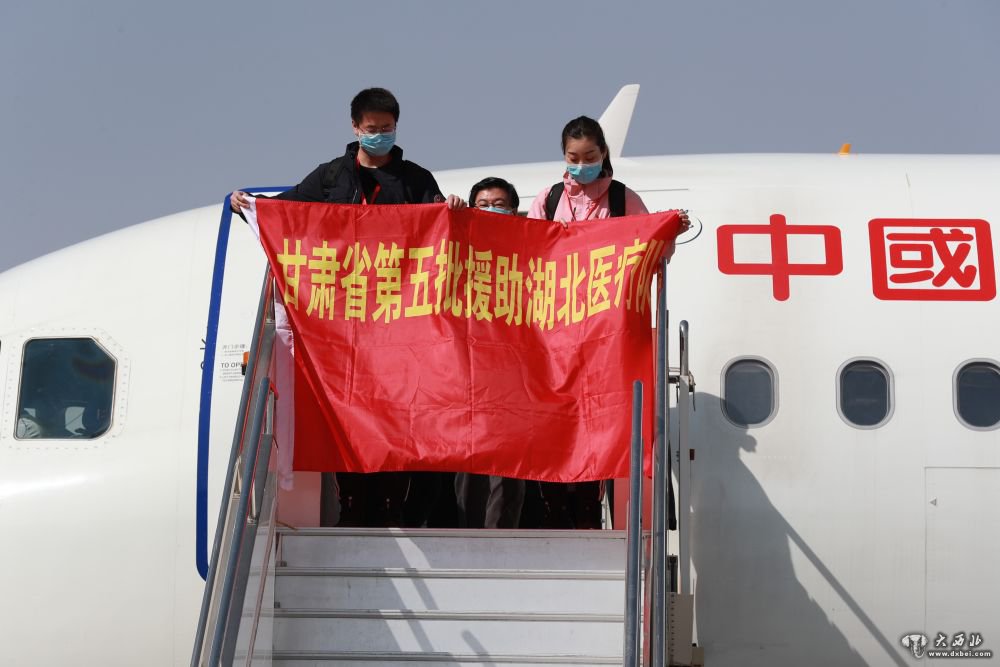我一仰面,满天的叶子,蓊蓊郁郁,像千万只纤纤绿蝴蝶,在光影里翻飞。叶的一面,呈淡绿色,随着风动,渐渐转亮。
古宅里的树,大都性格内敛,隐藏在古宅之中,如果不是有人走近,还不知道这儿藏着一丛花叶。
许多古宅里,都有一棵树。
归有光的“项脊轩”,就有这样的树。正像一场欢宴的刚刚开始,满月的夜晚,月上枝头,照过半截粉墙,桂树的影子交杂错落,微风徐来,花影娑动,说不尽的美好、欢愉。等到下半场,中途有人离席,谁知曲终人散,“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光影重叠,物是人非,剩下的唯有回忆。
《浮生六记》的作者沈三白,蜗居的姑苏城南沧浪亭,也有“老树一株,浓阴覆窗,人画俱绿”.散乱的线条,花影扶疏,映在方格门窗上,剪一帧温柔光晕,小窗幽幽,快乐寂寂。
古宅里的树,宜仰望。抬头信看,垂挂下一串串的璎珞,摩挲头顶。夏天的时候,水汽氤氲,“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总有几只小飞虫在光影里乱飞,满院花香扑鼻。树下,有两个人坐在那儿下棋。
人的年龄,抵不过一棵树的年龄;当主人不在了,树还很年轻。
一园,一树,一景。比如,我眼前的这棵千年桧柏,就站在两淮盐运使乔松年的宅院里。到过园子的人,有些景致变得依稀模糊,却记得这棵树。这棵树遭雷电所劈,半个躯干是空的,空着的躯干里,不知什么时候,贸然蹿进一只爬山虎,并且还在不停地向上蹿;另一段,仍艰难而迟缓地伸向天空。
树也风雅。所以,文人与树,窗前一团绿云,纸上一笼春烟;美人与树,梳妆镜里,一只翠鸟栖息枝头,婉转啼鸣。《红梦楼》里,摇曳着潇湘馆的竹、怡红院的垂丝海棠。
一棵树,就是一个人的前世今生。当主人还是孩童时,树就站在那儿,不知哪一个人亲手所栽?年少时,在那一棵树上攀爬,在清风中,抖落一串笑,摇晃着满地的繁花落叶,一地缤纷。长长的夜,庭院深深,风渐渐柔和,虫鸣歇息,唯有那棵树在微微呼吸。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等到老了,再回到宅院里,不知某个深夜,那棵树,跌落一串硕大的花骨朵儿,让人想到“闲庭落花”这个词。
江淮之间,有许多高大的乔木。有一年,在扬州何园,看到园子中间,也站着一棵高大的广玉兰,几百年的虬枝苍叶,像一把天然绿伞,遮盖了半个院子。与长江边上小叶乔木有所不同,它根部的经络,如一个老人的青筋毕现,吮吸着梅雨季节空气中湿漉漉的水汽。遥想当年才子佳人,站在二楼,倚栏而望,面对摇曳而至的玉兰枝,触手可及。
古宅里的树,还有石榴、黄杨、古槐、腊梅。夏天,石榴树开一树的繁花累果,照人眼明,给人“多子多福”的慰藉。冬天,那株老梅斜站在一口水井边,随风浮来清冽的暗香。至于那株黄杨,则站在一堆太湖假山石旁,细小的叶片,筛一地斑驳阳光。南方有嘉木,那棵树长得也慢,姿态优美,沐多少如水的月华星光。
当然,也有那些高大的树,不受一院的局限,比如香樟、银杏,站在路口、道旁,高大的光影,招来流连的目光。唯有古宅里的树,小巧、精致、静谧、拙朴,不事张扬。
古宅里的树,仰望的不只是花叶,还有天空纷纷而落的流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