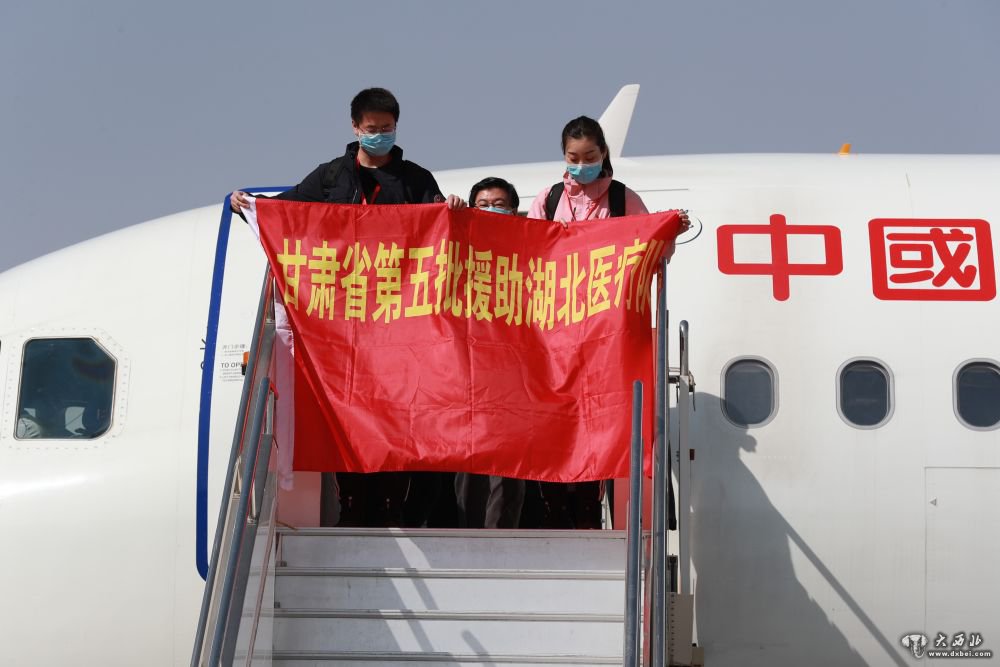我是几时认识明明的?仿佛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事了。那日古某人生日,请我去吃饭。古某与我有生意上的来往,欠我一笔微不足道的小债,他人是海派的,不知道为什么在生日那一天想到了我。是真生日还是假生日呢?于是我带了一瓶蓝带白兰地去。
我早到了,大家都是男人,古某的妻子也在,镶钻的白金劳力土表,一克拉半的钻戒、玉镯子,也就像个太太。居移体,养移气,每个太太都像个太太,就像我的妻子一样。我们坐在那里喝茶吃瓜子。然后便来了两位女客。一位大概四五十岁,珠光宝气,古某称她为“三姐”,然后古某看见了他“三姐”身后的女孩子,“呀”的一声,“你也来啦!”他有点意外,连忙介绍。
“朱小姐,”他说:“朱明明小姐。”然后把我们的姓名说了一番。
我看到朱小姐眼光闪也不闪,一只手串在三姐的臂弯里,根本不注意我们这些人。因为她不注意我们,所以我很注意她。她并不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女孩子。但是她有一张非常特别的、令人难忘的脸,她有那么圆的眼睛,平平的浓眉,嘴唇是翘翘的。头发烫得非常卷,而且刚洗过,还没有干。她的皮肤是蜜合色的,像一罐没有开盖的玻璃瓶装蜜糖,加上一点白脱油,随时会汩汩的、黏黏的流出来,无端沾了人一身。她的皮肤是她最美的地方。直到她笑,她的牙齿雪白。她穿了一套很古怪的衣裳,白色的,上半截不会比一个胸罩大很多,背后缚一个结,露着整个背部,下身倒是规规矩矩的一条裙子,都是白色麻纱通花的,脚上一双金色的细巧平跟凉鞋。
她脖子上有一条非常粗的十足金链条,刚刚圈在颈上,像那种埃及的女奴。左手腕上两只麻花金手镯,据说现在流行,纯金的配白色的。
她是一个骄傲的女孩子,即使尽量装得很随和,但是可以看得出她既不高兴又不畅快。她不抽烟,但是缓缓的喝着纯拔兰地,那一瓶是三姐带来的XO.
她不说什么话。
但是古某拖了一张椅子就往她身边坐,他嘴里说:“我陪明明。”也不管他太太高不高兴。
他太太并没有不高兴,她只是笑说:“明明越来越瘦了。”
朱明明只是笑笑。
三姐说:“像她这么好色的女孩子,焉得不瘦!”
我怔一怔,看着着她,她仍是笑。
三姐说:“你看她,本来一头黑鸦鸦的好直发,现在去烫成这个样子,像什么鬼。”
她还是笑。眼睛非常的寂寞。
她使我想起几句诗。是一个人写给他朋友的,诗忘了一大半,仿佛是这样的:
君初见我,
怪我落落,
转而因此,
赏我标格。
她就是这里标格吧。
要看笑容太便当了。有酒家、有舞厅、有按摩院、有急于要出嫁的女人,都会虚伪的、甜蜜的迎上笑来,笑得那么多,简直腻掉烦掉了。
我一向不肯花钱买女人。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自尊心的问题。我自问还没有到要出钱的地步。
当然钱的好处是快,不必慢慢的磨,打电话约会,喝咖啡,进一步拉手、接吻……两者我都觉得有弊有利,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做着一般人嘴里的好丈夫━━只会赚钱不会玩。
她还在喝XO,慢慢的喝,偶然也跟古某说几句话,古某总是被她哄得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我猜不透他们的关系。
后来还是古太太说了,“明明哥哥是我丈夫拜把子的兄弟,三姐也与我丈夫叩过头,那么明明又与三姐情同姊妹。”
我听了好一会儿才会过意来。然后我就微笑了。从她的眼神中看来,她怎么可能跟任何人“情同姊妹”,她原应是个最最无情的人。四周围的人她一个也没见到。她今天来了,是因为她想来,她想来是因为她想喝一点酒,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三姐问古:“这小子是谁?”指着是我。
古连忙说:“这是周老板,年轻有为。”
“这小子,尽微笑干什么?要是看上了我妹子,不妨出声。”
我连忙举杯,“我敬你,三姐。”
“好小子刘标,跟三姐挑战起来了,要是看中我妹子,非得先打通我这一关不可。”
我干了杯,说:“刘标干杯了。”
朱小姐明明在一边抿一抿嘴,长睫毛下的眼睛开始闪烁,但是不知道她心里想什么。
三姐说:“我妹子可是个特别人物,不比我是个做买卖开商行的,满身铜臭,人家是留学生,英国什么大学的艺术学院的高材生。”
我说:“呵,原来是艺术家。”
她不经意的笑一笑,只是牵牵嘴角,可以说根本没有笑,也根本不屑。酒越喝越多,她的神采越飞越远,不知道传到什么地方去了。但是我可以感觉得到她身上发散出来的寂寞,她仿佛是搽了一种叫做“寂寞”的名牌香水。
她把一切寂寞埋在心中,没有说出来。
英国。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很久很久之前,我有一个女朋友,她是皇家艺术学院的学生。日日我去接她放学,在雪地里等她。嘴中呵着白气,戴着皮手套还禁不住搓着手,这是我的习惯动作,倒不是因为冷,因为我没有一部车子。我有自卑。
我深爱着她,她是那么骄傲的女孩子。后来她嫁了人,嫁到美国乔治亚去了。我也很快的回家结了婚。可以说是为结婚而结婚的。女人都是狐狸,但至少也有老实一点的狐狸,我妻子是个一无所知的女人。奇怪,但凡做了妻子之后。女人都变得一无所知。因是我在家里放下了很多的心血与时间,至今五年,五年来我是个好丈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她要房子,我买房子给她,她要衣服,我买衣服给她。现在我们有一个三岁半的女儿,她又怀了孕,这个月底该生产了,希望是个儿子。
我不知道什么叫快乐,虽然我也快乐过。像多年前,我那女友答应我做圣诞舞伴。但那是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我的妻子喜欢打牌,而且喜欢把女儿也带了去。她是不能与我的女朋友比的,所以我做一个公平的人,我从来不将她们两个人相比。
但是朱明明坐在我对面,我忽然想起了我那个朝思暮想的人来,在雪地里,等她放学,而她终于嫁了别人。
饭局完了。
古他们还要去喝咖啡,我看看明明坐上了他的车子。我原本该回家的。十点半了,但是回去做什么呢?我见她去,我也去。
回家也不过是坐着,听着妻子说昨天因为一张白板的事而输掉三千台币。
我真没想到,过了五年,我唯一的快乐竟是想到当年在校园门口等一个并不爱我的女孩子。真没想到。难道快乐便就是这样的吗?难道这就是我日日夜夜所盼望的,而我现在不过是活在一个过渡时期的梦里?但是我的女儿有一张跟我一模一样的脸。处处提醒我,这将是我永桓的责任,直到我死。我有点麻木,我不太害怕,因为每个人都在这么做着,每个好丈夫肩上都挂着这么重的担子。每个比较幸运的女人都可以嫁到一个这样的丈夫。
直到我看到朱明明的眼神,像是一种审判的嘲弄的目光是吗?你们真的都那么快乐吗?你们都满足现状吗?你们都打算这样活下去吗?
我们到了夏蕙,一个菲律宾女歌手正在唱:
“──假如他向你要一个吻,
告诉他不不不,
假如她要约会你,
告诉他不不不,
告诉他你原属于我,
告诉他不不不──”
我们坐下来,每个人都有三分醉了。
三姐在那边说:“我们应该跳舞去,到新加坡去找几个小姐,陪着希尔顿去,来!”马上要开动的样子。
然后看没有人赞成,她便独个儿上台去唱了好几首歌。我并不觉得可笑,寂寞的人遍地皆是,看各人表现方式如何。能够发泄便好,像我,还得在全世界的人面前冒充是个最最幸福的人,最最不寂寞的人。你别看这些人疯疯癫癫的,最先崩溃的人必定是我。
三姐唱完歌之后硬是要叫明明把电话给我,明明大方的写了,我不敢接,把那张纸压在水果碟子下面。三姐半真半假的恼怒了,说:“我妹子哪一点配不上你?人呢,貌呢,还是才呢?你这混球可别把我给惹火了,我告诉你──”她作势要打,我只好赶紧把那张纸放进裤袋里。
古跟我低声说:“你也太没礼貌了,人家小姐既然写了,你怎么好意思不收下?”
我是不敢收,怕收下了忍不住要约她出来见她。
我看她一眼,她仍然是淡淡的,坐在那里,也不动,心中不知道想什么。
终于我们这一桌人又把一瓶拔兰地给喝光了,人家的店也打烊了,所有的人走在前头,我与明明落在后头。那三姐高声叫:“送我妹子!”
我向明明笑笑。
她简单的问:“我们上哪儿去?”
我吃一惊,随即平服下来,酒能壮胆。上哪儿去?
她更简单的说:“你要是不反对,我们都不回家。你要是有顾忌,我自己叫车回去就得了。”
她的发卷干了,吹在风里,另有一股韵味。我拉住她的手臂,皮肤像缎子一样的,我拉着她过了马路,到一间中等的旅馆,开了间房间,便带着锁匙上楼。
我们认识才八个小时,说了十句话,便发生了关系。
她是一个美丽而勇敢的女子。
但是她的心事,永远不会为我所知。
有这么一个倩人,是每个男人梦寐以求的吧!有知识的、有容貌的、够姿态的,但是我负担得起她吗?精神上、心理上。
我记得她柔软的嘴唇,我要问她:你可知道我的名字?但是何必呢?我老婆知道我的名字,但是她却不知道我的心。
我握看她的手,我熟睡了。
醒来,她已经不在了,她几时走的,我根本不知道。我连忙赶回家去,老婆以古怪的神色看着我,不动声色,觉女儿来跟我说:“爸爸,不要常常出去喝酒,常常回来陪我们。”这些女人啊,连三岁的孩子都被她们利用了,给了她们家庭,她们要人,给她们人,她们要钱,给她们钱,她们要你的灵魂。
我老婆虽然没有什么知识,但她是一个厉害的女人。很爱说话的,最最没有用的女人才往往是最厉害的女人。她非到必要时是不与我大吵的,她尽量装个小媳妇状也不肯露出她的泼辣。她明知我这一辈子最错的一着便是在心伤之余与她结了婚,她也知道她的出身。一个男人在最最寂寞痛苦的时候,难道还有心思去找一个社交名媛作太太吗?她是欢场里一个比较清爽的女人。我把她拉了出来,结了婚。但有时候她也忘了过去的事,她现在名正言顺的做了五年的周太太,有时候我真正因公事晚一点回家,她会说:“你是吃定了我了!”
我想,这句话,我觉得一句是我的错,是我把她娶进门的,大多数的时候,她还是一个识趣的女人。譬如我去香港,给她带回来衣服,她总是装得很喜欢的样子,是不是真喜欢,我并不知道。
我把口袋里的小字条掏出来看,纸上写看她的电话号码,她的名字。我才发觉她不是叫朱明明。她是叫朱明冥。一半明,一半冥,像她的人吧。一半一半。
我是否应该再找她呢。在她面前我有自卑感。凭什么呢,因为我的虚荣感?因为她的寂寞?
晚上七点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她,“我约了两三个朋友吃饭,你可以出来吗?”
“可以。”她说。
“七点半我到你家门口接你,请你把地址说一说。”
她说了,说得很详细,证明她是办惯事的人,非常的老练而且爽快。
她的声音是淡的、冷的,一切希望都没有的,洞悉了整个天地。
好像昨天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昨天不过是握了一下手,根本就是,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把那件事看得那么重要。
我找到了古某,与他聊了一会儿。
他知道我的目的是要打听朱明冥,这个世界上聪明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了,他说:“家里有点钱,毕业回来了,闲着也是闲着,你叫她到什么地方去找工作?无聊得很,男朋友非常多,名誉也非常的坏,但是现在的人并不计较这些了,她是很特别的,我如果不是与她家里有太深的关系,也很想追求她。”他呵呵的笑了。
我挂上了电话。
但是我找她的时候,她在家,她并没有出去,并不像有很多男朋友。
追求通常的目的是男人把女人追到床上去,但是对她来说,那不算什么,追求是追求她的心她的思想,我有这个能力吗?恐怕一辈子也不能够呢。我忽然非常反悔晚上约了她。而她居然很大方的答应了。
我去接她的时候,她站在家门外的巷口,黄昏。她家那条巷子密密的是桂花树,她人站在那里,很准时,一派外国作风,一身白衣,裤子是束脚管的,益发像个古代的女奴打扮,是她自己思想的奴隶。她并没有笑,我替她开了车门,她坐在我身边。我看她一眼,她也看看我。
我问:“我们今天去吃川菜好不好?”
她简单的说好。
我看她的手,她的手握着一只精致的皮包,手相当的大,手指甲上没有搽任何东西。她是个倔强的人,毫无疑问。
我问她:“打算在台北耽多久?”
“不走了。”她说。
“呵。”我说,我希望她走,走得远远的,那么我身边便少了一个诱惑。
“平常做些什么?”我问。
“不做什么?”她说:“看武侠小说。”
她忽然笑了,展起颜来,像个小孩子,眼睛又大又圆又别,这么美的一个女孩子。
“你几岁?”我忍不住问。
“我不回答。”她说。
“我一问就问出来了。”我说:“我去问你三姐,去问你的朋友,去问──”
“你不会的,你是一个有太太的人,你而且是一个好丈夫,你不会忙着去追究另外一个女人的年龄。”
“怎么见得我是好丈夫?”我忽然之间非常的惭愧,“好丈夫怎么会背着妻子跟人家私会?”
“那并不影响好丈夫的成份,”她说:“一个男人可以娶十个老婆,只要那十个老婆都认为生活满意,那就是个好丈夫。我的定义非常的简单。”
“但愿每个人都如你这么想。”我纳罕的说:“我真奇怪,你没有占有欲。”
“是的,因为我没有恋爱过,爱我的人,我都不爱他们,我爱的人,都不爱我,所以我乐得故作大方。”她笑了。
“你爱过谁?”
她问:“譬如说我爱你,你相信吗?”
我怔住了,我没想到她会这么问。我说:“我们相识才短短的两天不到,你有考虑过吗?才四十八小时不到。”
“时间不是因素,时间永远不是因素。至少对我来说,不算一回事。”她转过了头,眼睛不看着我。
我知道她觉得无法与我的语言交通。她的思想我无法接受,我的思想她看起来可能是太俗太俗了。
我把车停下来,扶朱明冥下车,在灯光下,她的脸说不出的美丽柔和,但是她永远不可能属于我,再美的东西,如果不是我的,又有什么用呢。我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我不能够高攀她。
她是一个很得体的女孩子,我的朋友们都十分欣赏她,她似乎什么都可以说上一阵,有一意无意间表示了她的意见,非常坚决的,但是用柔和的口气说出来。
晚上我送她回去。我把车子朝她家的方向开出去,她并没有反对。须把车停在路边,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非常的沉默。
“你在想什么?”我问。
“我在想,如果我嫁了你,我或者会做一个好妻子。”
“你说谎,你才不是在想嫁给我。”我说。
“你们为什么都不相信我?”她扬扬眉毛,声音很平淡,“我是一个很寂寞的女人,台北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我没有男朋友。这种时间空间使人容易堕入爱河,你不认为吗?”
“在什么情形之下不容易爱上一个人?”我问。
“在上大学的时候,忙碌的功课,忙碌的校外活动,到处是嬉笑的,可以交通的人,宿舍里、校园里、课室里,教授、同学,甚至是收拾房间的工人。来不及的写功课交功课考试升级,抢着看电影过节旅行,哪来的时间看身边有什么可爱的人,生命还没有开始,生命要由我来改革,由我自大学出来慢慢改革。”
我听着她。
“所以我失去了他。”她说。
我抬起了头。我问:“我像他吗?”
她笑:“不。你不像他。”
“你为什么选择我?”我问。
“我喜欢你。”
“如果我不是出言逗你三姐,你是永远不会注意我这个人的,是不是?”
她问:“为什么男人都有这么大的自卑感?”
“你太强了。”
“我并不是。”她说:“我认为男人会喜欢挑战。”
“不是在这方面。男人在女人面前永远要做一个强者。”我说:“女永远不会明白,男人往往比女人更需要安全感。我并不骗你。”
“所以即使是找情妇,你也不会找我。”她说。
“我连一个太太都养不起,有什么资格养情妇?”我苦笑。
“我明白了。”她说。
“你明白了什么?”
“你不要再见我了。”她说。
我深深的震惊着,因为她猜中了我的心事。
“我不会埋怨你。我会想起你。”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平淡。
在灯光下,她的脸是完美的。我是哪一国的傻瓜?不好好的抓紧她?我有这个机会,到年老的时候我会后悔的。我真的会。
她又笑了一笑,她说:“我想你们男人叫这种为‘艳遇'.”
“你不算。你真的不算。”我握住她的肩膀,“明冥──”
“我懂得我明白。”她说:“没有什么分别了,我在这里下车如何?”
“我是一个结了婚的人。”我说。
“你是一个好丈夫。”她说:“再见。”她开了车门,下了车,笔直的向前去。
她在巷子角落消失了。
我忘了问她:“在夏天,你每日都穿白色吗?”
我相信是的。
自那日起,我没有再去找过明冥。我的工作很忙,我家中也很忙,但是我时常想起她。她的一身白衣服,她那种精神永远不集中的样子。她那双洞悉一切的眼睛。
每当我在静下来的时候,我马上会想起她。
在街上,我看到卷发的女孩子,我会害怕惭愧地避过,但是马上的反应是想看清楚她是不是明冥。我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了。我没有再见到她。
后来我见过古某人了一、二次,我们没有提及明冥,两个大男人提人家一个女孩子的名字,是很不应该的吧?我很惶恐,我怕永远永远见不到她了。
妻子生产之后,我们与友人同去夏蕙喝酒,那个菲律宾女歌手在那里唱一首异常熟悉的歌:
“如果她向你要一个吻,
告诉他不不不,
如果他要约会你,
告诉他不不不──”
我忽然之间醉了疯了,觉得一切都不再重要,我马上到公众电话去投下一个硬币,打电话过去给明冥,即使只是再听听她的声音也好。
我居然还记得那个电话号码。
电话铃声晌了很久,一个女人来接电话,本地人的口音,向我解释着那个小姐搬走已经很久了。我握着话筒,眼泪忽然汩汩流了下来。
我放下了话筒。
那个女歌手继续唱:
“到派对去是可以的,
找点乐趣是可以的,
但是别挑他做爱人,
如果他要带你回家,
告诉他不不不。”
我哭着,头靠在手臂上。我非常爽快的哭了很久。
妻子并没有问我为什么。
第二天早上她只是告诉我:“你昨天哭了。”
我微笑,“是吗?”我平静的问:“我一定是喝醉了。”
“是了,你喝醉了。”妻子肯定的说。
女儿歪歪斜斜的走过来,快四岁了,她说:“爸爸别出去喝酒,爸爸在家陪我们。”
刚出生没多久的儿子躺在隔壁的婴儿房里。
我也很肯定的说:“我喝醉了。”
别关冷气,夏天还没有过。
我忘了问她:“在夏天,你日日都是穿白色的衣服吗?”
她的身影在巷子转角处消失。那条满是桂花的巷子。我原来可以再抓住她一段时候,原本是可以的。
但是我已经结婚了,两个孩子。我不能对她那样,真的不能。明年夏天会是什么样子呢。把夏天留住,把时间留住,把她留住。不不不,我还是一个年轻的男孩子,傻气的在恋爱中。把时间留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