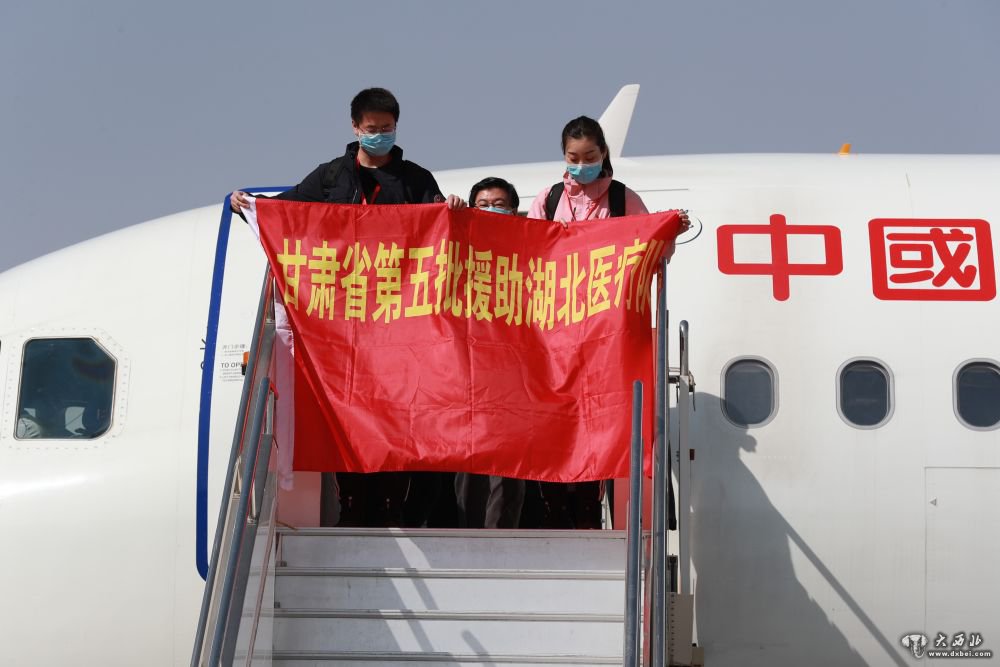我16岁那年,爸爸去世了。一年之后,我们搬回市里居住。母亲靠替人打扫房间维持全家生计,同时还要偿还爸爸生前欠下的债务,供养我读完大学。
母亲身上有着工人阶级特有的强烈的自尊心。爸爸走后,“整洁”与“卫生”,就是她的人生追求。她虚怀若谷,忠诚坦荡,一丝不苟,始终固守着她那些崇高的行为准则。人们开始对她刮目相看,凡是经过卡罗尔·兰打扫过的房屋,间间都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在沿河两岸的郊区,她的名字家喻户晓,是个难得的、最受人欢迎的清洁工。
20年来,母亲仅仅因为一副丢失的耳环被解雇过一次。那一次,户主让她一周后离职,她回家后独自一人站在屋外的那棵柠檬树下哭泣,生怕被我听见。我试图劝她不要再去干那最后一周的活了,可她就是听不进去。
她准备回去为那个户主继续干活的早晨,我们又争吵开了。接下来,我在浴室里洗澡,她则立在门边给我上课,告诉我什么才是做人的尊严,好像我根本就不是年已20岁的法律专业大学生,而是一个整天需要大人呵护、-乳-臭未干的小毛孩。
“真是顽固透顶!你要去就去吧,别想要我帮你!”我叫道。
“我可没说过要你帮我,”她说,“我啥时候说过要你帮我了?”
我低声叹息,无言以对,还是默默地跟着妈妈上了车。
车子里散发着漂白粉和橡胶手套的气味。我重重地呼出了一口气,摇下车窗。母亲那双饱经磨难、已是粗糙不堪、不成样子的大手,正稳稳地握着方向盘。她的下巴微微翘起,神态稍显愚笨,但却带着几分威严。
“你能跟我来,真是太好了!”
“唔--寻思着你需要个帮手。”
“哦,不是帮手,是爱,是亲情哪!”
我对妈妈的怨气未消。这她看得出来。
“我知道,做人很不容易,”她说。
“可你这是在委曲求全,是在给人低三下四啊,妈妈!”我已经顾不上心中存有的顾忌,脱口而出。
“是在给谁低三下四?”
“是谁诬陷你偷东西了?还说要解雇你,叫你一周之后离职,好让她有时间去物色*其他人来接替你的工作?”
“无论如何--我们要用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才是。”
“您是说……”
“我们要给那套公寓来一次彻底的清扫!”
我斜拉着双眼,钻出车门,从后座上提起真空吸尘器;妈妈则拉出一只水桶,里面塞满了抹布和挤水瓶,还有拖把。
公寓里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显然都来自困居家中的几只小猫咪。妈妈径直去了厨房。听到有撕开信封的声音,我走进厨房,看见她手里正拿着一张紫红色*的信笺,她将信笺塞进了口袋。信封就在长凳上横躺着,里面装着钞票。
“猫垫,”她说。
我走进洗衣间。里面没有通风口,空气混浊不堪,给猫作窝用的垫子就搁在钢制水槽下,其臭难闻。我手中提着一只垃圾袋,弯下腰来,并改用嘴巴呼吸,却让飞扬的尘土钻了空子,弄得嘴唇和舌头都是灰,令人作呕。
在浴室的那边,妈妈在哼着跑了调的歌儿。我在门口停留了片刻,只见一股雾状的氨气正在漫过前厅,非常刺鼻。似乎是意识到了我的存在,她颤抖的歌声停住了。她面朝浴缸,弯着腰,双手粗壮有力,腿上布满了青筋。我往前挪动脚步,后面传过来她擦洗浴缸时所发出的急促的呼吸声。
我将垃圾袋放入塑料箱中浸泡,除去脏水,但垫子上尽是污垢,很费工夫。母亲不时过来认真查看,就像个军士长在战场上审视着列兵。妈妈和我都认为:要是由这家女主人亲自来打扫,肯定要用上一个礼拜的时间。
妈妈还在厨房里忙碌着。然后她到卧室,看到我正跪着用吸尘器在打扫被褥上的花边装饰和拼缝物。
“说真的,妈妈,我们为何不马虎一点儿就算了?或者你应该把耳环的事告诉警察,让他们去我们家搜查好了,这样也好弄个水落石出。反正,人正不怕影子歪!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人言可畏呀!要知道,谣言说上百遍,就会变成真理。如果是这样,下一回谁还敢雇用我呢?”
她留着狮子式头发,脸上的汗珠闪烁着光芒。过去,妈妈也曾经美丽动人。
“所以,你现在就得两头受气!”
我摇了摇头,再次打开吸尘器的电源开关,对准床下的地毯猛烈轰扫。突然,吸管内好像有什么硬东西在发出异响。
我撬开吸尘器的盖板,用手在装满垃圾的吸尘袋中摸索着。不一会,在那些卷曲的棉绒、毛发和污物中,露出了一只耳环。
“瞧那下面!另一只肯定就在附近!”
在壁脚板处,我果然找到了另一只耳环。
“好了,你现在总算得以洗冤了。”
她说道:“要知道,维克多,我目前得到的一切回报,就唯有这么一点好名声了。”
我转头看着地板,耳边听到母亲在擤着鼻涕。我不知如何才能给母亲以最有力的保护,心中很不是滋味。
“我这就去把厨房的活干完,”她说道,“10分钟就好。”
我再次启动吸尘器清扫卧室的其他角落。那副耳环就放在床上。我瞅了它们一眼,果然是非常漂亮,只可惜,我对珠宝一窍不通。莫非,它们的真正价值,就是让妈妈白白地遭受莫名的痛苦和烦心?
在厨房,妈妈已将抹布和挤水瓶装入水桶,就要动身了。临行前,她跪下身去,用一块毛巾把地板又擦拭了一遍。
“那些钱呢?”我问道,一边看了看妈妈擦洗过的那张长凳。
“我的身价呀,可要比这些钞票值钱得多!”她说道。
“你没拿?”
“没有拿!”
我微笑着,摇了摇头。
“吸尘器你忘记关了。”她最后说道。 “哦--好了!”
车门已被打开。旁边,是母亲高大的侧影,蹒跚的脚步正透过明媚的阳光。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跟着她钻进了汽车。时值下午,车子外面,正是骄阳似火,炎热非常。